婚外情似乎是文学作品最常涉及的话题我真是大明星绿帽版h,缘故原由 是托尔斯泰在婚外情的经典著作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精炼 总结指出的: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”。既然我们看小说更喜欢图个新鲜,那么谁愿意书中男女展示着一样平常 生涯 向我们秀恩爱呢我真是大明星绿帽版h?以是 一个童话写到“王子和公主以后 幸福地生涯 在一起”就可以打住,花式虐狗的细节我们没兴趣知道。不外,要是有个“圈外人”泛起,这故事就可以越写越长,继续吸引我们的眼光 ,由于 各人更为关注的好戏就要开场了我真是大明星绿帽版h!《道德经》上说,“三”生万物,真是所言不虚。
在关于婚外情的文学作品中,《奥赛罗》可能是最冤的一部,由于 坏人的蛊惑,奥赛罗嫌疑 自己的妻子出轨,可怜的妻子由于 莫须有的婚外情被恼怒的丈夫活活掐死。观众们全程知道妻子的无辜,以是 会同情,会恼怒。然而若是 妻子真的有婚外情呢?故事会不会酿成吃瓜群众一起兴奋地喊着:“掐死她!掐死她!”家庭的不稳固 总是让人恐慌的,斯特林堡的剧作《父亲》中,由于 嫌疑 孩子不是自己亲生,这个念头活活逼疯了一位父亲。一个家庭训斥 婚外情的义正词严,与一个民族处罚叛徒是很相近的,摩西在律法上早就付托了:把这样的人用石头打死!不外西方仍然有另一种看法,来自耶稣:有一个女人行淫时被拿住了,有人问耶稣,该把她怎么样。耶稣的回覆是:你们中央 谁是没有罪的,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。于是各人都默默走开了。耶稣的泛爱简直是伟大的,不外我以为 这些观众的忠实 也一样伟大,而且,从世风日下的当今看来,更为难堪 。
每个民族对婚外情的态度都不尽相同,这和社会制度息息相关,也受制于人们对道德的差异条理的明确 。在父权制社会,一个男子 三妻四妾眠花卧柳似乎并不受指责,甚至令人艳羡,风骚韵事成了社会职位的象征,而“河东狮吼”却惹得人讥笑。不外我信托 讥笑的一定 多数是男子 ,多数人以为 有特权而不享受特权的理由一样平常 有三种:不愿,不敢,不能。第一种那是要做“大事”的人,例如柳下惠可以坐怀不乱,以是 被誉为贤人 ,宋江更喜欢结交兄弟,以是 不近女色,甚至为了保全江湖义气狠心杀了阎婆惜;第二种常被笑称“没种”,例如被苏东坡写诗嘲弄的惧内的陈季常;但真正的“没种”原来应该是第三种,即没这个功效,例如就有人嫌疑 柳下惠是不是性功效障碍者。对男子 婚外情的宽容,对女性圈外人的歧视,本质上虽然是一种精神不一律 ,由于 每一件这样的事情发生,理论上总是有一男一女,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女人?虽然中世纪已经竣事 了,但中世纪男尊女卑的头脑 方式,似乎还流淌在许多人的血液里。
我们习惯为一切婚姻失败寻找圈外人,似乎圈外人这回事是“理所虽然”的,然而尚有 一种在通俗 人心中“不行理喻”的婚外情。例如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中以画家高更为原型的斯特里克兰,《刀锋》中听说 以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原型的拉里。毛姆笔下的另类“婚外情”,男子 并非爱上了此外什么女人,而是爱上了一个梦想,艺术的梦想,哲学的梦想,虽然也有人是宗教的梦想,例如“抛妻弃子”出家的李叔同。梦想和梦中情人一样充满诱惑,而且,可能比现实中的男女更具诱惑,由于 梦想永远不会变得“有心无力”,遭遇“人老珠黄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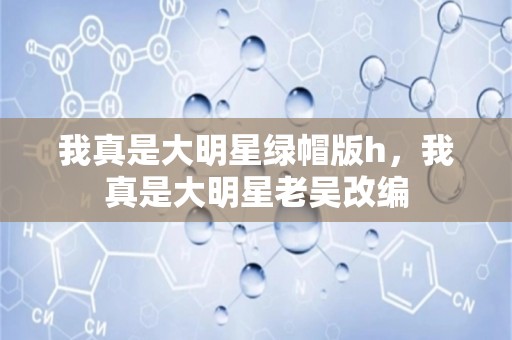
虽然,毛姆写的都是特例,是成人的“童话”,天下 名著中的大部门婚外情,仍是浮世男女之间的恩怨情仇,有人引以为耻,有人因之自得,皆因差异国家,差异民族,差异个体的习性使然。
东方,中世纪,偷情的优美 时代
同样是“中世纪”,日本与中国在男女问题上的看法生长截然不同 。中国至少在唐代以前,私奔偷情婚外恋,那都不是事,由于 那时间 提倡自由恋爱。《唐律》中有划定:子女未征得家长赞成 建设了婚姻关系的,执法予以认可,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父老算作违律。再加上其时女性职位较高,享有与男子一律 的婚外偷情的自由。执法和民俗都为青年男女自由选择戴绿帽开绿灯。宋代之后,贞操看法才一直 强化。
古代日本的民俗习惯多模拟 唐代,女性魅力除了文采风骚,性魅力也是主要 的权衡尺度。平安朝的女才子清少纳言在《枕草子》中就写了偷情的优美 :“神秘 去会见情人的时间 ,炎天 是特殊 有情趣。很是短的夜间,真是一下子就亮了,连一睡也没有睡。无论什么地方,白昼里都开放着,就是睡着也很凉爽地看得见周围 。话也照旧有想说的,相互说着话儿,正这么坐着,只闻声 前面有乌鸦高声叫着飞了已往,以为 自己照旧清清晰 楚地给看了去了,这很有意思。尚有 ,在冬天很冷的夜里,同情人深深缩在被窝里,听撞钟声,似乎是从什么工具底下传来的响声似的,以为 很有趣。鸡声叫了起来,早先 也是把嘴藏在羽毛中央 啼的,以是 声音闷着,像是很深远的样子,到了第二次第三次啼叫,便似乎近起来了,这也是很有意思的。”真是无冬无夏,约会一直 。尚有 一位文艺女青年和泉式部,老公移情别恋,于是她靠着仙颜 加才气不光俘获了许多男子的心,还以“小三”上位挤走了亲王的正室。这在她的日志 中可是“恬不知耻”地纪录着。
相对而言,紫式部的私生涯 就显得洁身自许多几何了。但在《源氏物语》中,她的“三观”也并不守旧,整本书都是光源氏瞒人线人的偷情暗恋,作者虽语微含讽,但却不以为忤,甚至可能把光源氏视作“脂粉堆”中的英雄。或许所有中世纪能发生的不伦之爱都能在《源氏物语》中找到,只要这爱切合审美需要。但紫式部的高明之处在于,除了欲望自己,她同时也看透了欲望本质的苦恼。
《源氏物语》,[日]紫式部著,林文月译,译林出书社
文艺再起,性自由作为梦想
东方和西方的中世纪,性自由都只是少少数人的特权,对公共而言,不道德的行为是地狱之门。于是早期文艺再起,对人性的张扬就成了拨乱横竖的应有之义。如意大利《十日谈》中的天下 ,性自由就是作为一种梦想,而且是一幕幕热热闹闹的笑剧 。
书中一位因婚外情被告上法庭的女性,面临 法官的询问,她的回覆是:身为世间的饮食男女,若是 在家吃欠好吃不饱,就只有到外面果腹解渴了。法官以为 她说的有理,宣告她无罪释放。丈夫不光“人生苦短”,还要因此忍气吞声戴绿帽。《十日谈》整本书都似乎在赤裸裸地宣告:欲望无罪,偷情有理。这样为所欲为 的好日子,即便在西方,生怕 也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《十日谈》,[意]薄伽丘著,王永年译,人民文学出书社
十九世纪,婚外情作为梦想的破灭
文艺再起只是短暂再起了欲望,男女关系乱了一阵后,西方就最先 了宗教刷新 。所谓宗教刷新 ,并不是作废 基督教,而是消解中世纪宗教不近人情、禁锢人权的专断权威,重新合理制约被解放的人权。这种合理制约延续至今,在维护通俗 人的心灵生涯 上有其不行消逝 的孝顺 ,但对纵容 自由的艺术家们来说,就显得有那么点儿不够友好,在他们眼里,狮子和绵羊共用一部执法,就是专制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,有谈论 家把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称为女性的堂吉诃德,是极有看法的。堂吉诃德由于 读了骑士小说,要实现书里行侠仗义的理想;包法利夫人由于 读了恋爱小说,而一心追求恋爱的梦想。但正如现实的风车不是堂吉诃德眼中巨人一样,现实中的婚外情也没有书上形貌 的那么优美 ,最最少 男子 没有书里那么优美 。包法利夫人为“人性解放”的梦想而做的起劲 ,只好无情地撞碎在现实的南墙上。
对此,福楼拜用一种近乎看客的事不关己、不动声色的岑寂 和冷淡 ,冷冷看着包法利夫人偷情、遭情人遗弃、欠债、仰药自杀,看着一个文艺再起时期被作为笑剧 的梦想灰飞烟灭,成为悲剧。我们看多了文学家写的天下 ,总以为社会民俗 比我们想象的更先锋,着实 那只是文学家的三观走在了时代的前面。托尔斯泰在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中对女主人公的同情,是作者伟大的体现。而《包法利夫人》中近乎冷漠 的岑寂 ,更是一个时代关于婚外情看法的一个整体象征,是作品伟大的体现。
《包法利夫人》,[法]福楼拜著,许渊冲译,译林出书社
二十世纪,被部门一定 的世俗欲望
到了二十世纪,被欲望折磨的世俗男女都应该谢谢一个“神”,他叫弗洛伊德。自从他给人类的原罪重新命了名,我们就重新受了洗,以后 我们再也不叫“原罪”,改了一个高峻上的名字——“力比多”,真是又温柔又性感。
被理性的天主 拍碎的情绪 梦想,由于 弗洛伊德而得以苏醒。“力比多”外貌上看图谋不轨 ,总是扒了裤子往男男女女的下半身指指点点,但它骨子里却是极其宽容、极其夷易 近人的。理性虽然带给人类启蒙,但绝对理性却往往走向理性的专制和理性的疯狂。“力比多”则使人回到充满人情味的一样平常 幸福,消解禁欲主义给人格带来的扭曲。由此,劳伦斯唯美主义的偷情文学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虽然曾以“有伤风化”的罪名被查封,但终究照旧解禁了。这是文学的胜利,部门苏醒了《十日谈》所张扬 的世俗欲望。
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,[英]d.h.劳伦斯著,黑马译,中央编译出书社
但欲望的苏醒绝不能矫枉过正,由于 理性告诉我们,婚外情也一定会带来它造成的效果 ,也是弗洛伊德早就告诉过我们的——心理创伤。同为德语天下 的作家君特·格拉斯,在婚外情事务 中就更为关注其对家庭职员 所造成的心理创伤,尤其是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在这一大人的任性行为中遭受 的恶性影响。《铁皮鼓》中的小孩,由于 眼见 了母亲的婚外情而拒绝长大,这可能会是婚外情家庭的孩子普遍存在的潜在问题。大人们不用一厢情愿地强调自己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认真 ,由于 有些行为一旦由人构置出来,甚至也就不以当事人的意愿为转移了。我们虽具备造成恶果的条件,却往往并无摒挡 恶果廓张的能力。人的欲望是应该被部门一定 的,但理智资助我们的,可能更多。
《铁皮鼓》,[德]君特·格拉斯著,胡其鼎译,上海译文出书社
